桑东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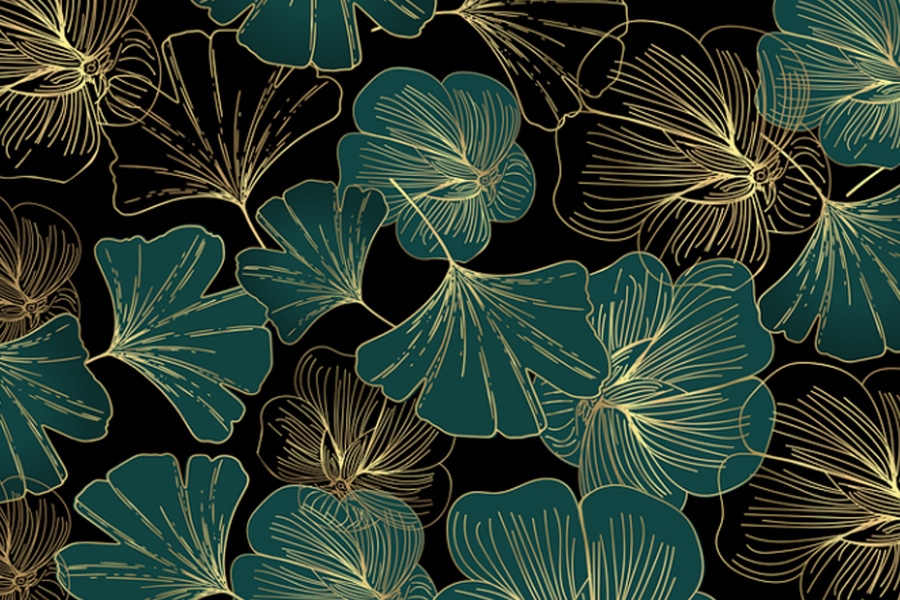
“一切没有出现过,一切也存在了。”我第一次读到这句富有哲理的话是在与90后女作家杨知寒的微信交流中。具体说来,是从她反馈给我的信息中看到的。我没有问过杨知寒这句话是出自哪个名人或哪部文献中,也不知道这句富含禅语机锋的话是否出自其本人的个人感悟,但我却深深被这句话触动了。是呀,这世间的事有时就是这么玄妙和魔幻。有时候,我们执着于某件事或某个事物,但其实它并非如我们想象的那样,它只存在于我们主观的感知和想象中,一如《寻金之旅》(《钟山》2023年第2期)中那影响李燕生至深且纠缠不已的金货。
在与杨知寒的交流中,她还一再谦逊地说自己并不深刻,写作也是由着性子,没什么深刻的考虑。但我想如果一个能说出“一切没有出现过,一切也存在了”的人都不算深刻的话,那肯定是我对深刻这个词的理解出现了偏差。至少在杨知寒的近作《寻金之旅》中,我们能从凡人琐事的生存苦恼乃至人伦亲情的纠结中,寻绎出一个人的蜕变和一个家庭的崩解,深切体味到“一切没有出现过,一切也存在了”的深刻哲理。
只看“一切没有出现过,一切也存在了”这句话,往往会觉得有点故弄玄虚,但当读过作者的《连环收缴》《黄桃罐头》《美味佳药》《水漫蓝桥》等作品后,就会理解这句话的深刻涵义了。在《寻金之旅》中,杨知寒秉承了自己一贯的冷峻、深刻的叙事风格和亲情淡漠的人物形象设计,在一个家庭的寻常故事中很好地诠释了“一切没有出现过,一切也存在了”这句话所包含的存在主义哲学意蕴。
在《寻金之旅》中,李燕生作为个体的存在,其也是“是其所是”的,虽然她的生活是那么的荒诞:由一个朗诵课文能给人带来无限美感的优雅语文老师变成一个撒泼打滚、犯浑耍横的放高利贷者,由一个长相清秀、仿佛“天外来客”般美丽的女教师蜕变成一个满身散发铜臭味、满脑袋长癞疮的吸血鬼。因生活的重压(原生家庭的疏离和隔膜、丈夫因一次意外被打折腿而变得魔怔等)和金子的异化,李燕生一下子就由一位受人尊敬的人类灵魂工程师变成一个为人唾弃的放贷者、逼债人,变成当代“黄世仁”,其生活状态也如薛定谔的猫,处于人不人、鬼不鬼,死不死、活不活的半死不活状态,其灵魂在现实生活中被悬隔起来,无所归依,无所依傍,迷失了自我。
从某种意义上,《寻金之旅》是一部反映家庭伦理和亲情关系的短篇佳作。它的高明之处在于通过李燕生这个人物颠覆性的人生巨变揭示了人性的复杂,探索出一条人的自我觉醒、自我救赎之路。李燕生的人生因得金、守金被套牢,也因寻金而得到救赎。如同那埋在地下的金货一样,她也曾长期将自己和自己的整个人生乃至整个家庭埋在了利欲熏心、烦恼丛生的寻常生活里,从而销蚀掉自己的青春和热情,蜕变成一个冷漠、刁狠、邋遢的放贷者、吸血鬼。最终,当因家庭畸形而走上邪路的儿子谭凯在车祸中躺在病床上急需花钱治病时,李燕生在反复激烈的思想斗争后,经过对自己一生的全面回顾和冷静反省,终于亲情战胜了薄情,人性战胜了物欲,在未泯的良知驱策下,准备拿出埋在地下的金子去救儿子。但戏剧性的一幕却出现了:金子走了。可以说,从李燕生父亲和家人求李燕生拿出金子帮助家庭走出困境,到李燕生的儿子谭凯偷着挖金子而未果,再到李燕生最后为救儿子而下决心挖金救子,演绎了一场寻金之旅。而李燕生最后的挖金行为尽管因为“金子走了”而失败,但李燕生却因此而完成了自我救赎。
记得东晋殷浩回答桓玄时有句经典的话:“我与我周旋久,宁做我。”这是《世说新语》的说法,在《晋书》中,殷浩这句话是“我与君周旋久,宁做我”。李燕生的一生不知道是自己与自己在周旋,还是自我与他者、与这个世界在周旋,但她确实始终在做自己,尽管做得很不堪,做得前后不一,甚至判若两人。在李燕生身上,年轻时的清丽脱俗与中年时的阴冷诡异形成强烈反差,那曾经声情并茂朗诵课文的优美音色与讨债时混不吝的阴鸷冷漠形成明显对比。归根结底,在亲情淡漠家庭中成长起来、曾希望与谭家秋建立一个温暖和谐家庭却因谭沉迷于无谓的诉讼而未果的李燕生,最终为了做那个所谓 “自己”,而牺牲了生命中曾经的美好,放失了自己的善念和良知,走上了一条前后迥异、南辕北辙的道路。在“以他人为地狱”的人生中,李燕生把自己的人生活得虚无而真实。某种程度上讲,人的存在是虚无的,本身似乎并没有什么意义,但人的存在又是真实的,人存在的意义就是人本身。李燕生的生存意义是依附于那若有若无的金子之上的。如果说金子是李燕生生存的目的,同时也成了她生存的手段,是她赖以生存的精神依托。但她只见金相而不见金体。不知道最终李燕生当发现金子不见了时,是否会体悟到金子本身也是空有不二的,也即金子本来就没有存在过,但也从没有失去过。
这里插一句,在《寻金之旅》中,曾出现过李燕生挖出一部分金货盘下杂货店的情节。我认为这个情节实际上与故事的主题关联不大,如果金子从来没有出现过,甚至没有被实际挖出过,也许叙事效果会更好。这样更增加了“一切没有出现过,一切也存在了”的魔幻性,也更能反映出在现实面前,不仅谭家秋魔怔成一个精神病,李燕生某种程度也是活在虚幻中的妄想症患者。当然,这些只是我的一点理解,而小说的作者更关心的是一种灵魂层面的失重。
所谓“顺从自己的代价,是灵魂失重”。在《寻金之旅》的创作谈(见2023年4月11日的《钟山》微信公众号)中,杨知寒用了《失重》这个题目,并由衷地慨叹道:“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顺从自己的代价,是灵魂失重,让至亲至爱的人都渐行渐远,哪怕她其实多渴望亲近。”随后,杨知寒又给出了答案:“此刻,我又一次想,人性是疑云遍布的星球,我们互相窥看,在各自的轨道旋转,最贴近的时刻,也鲜少真带来安慰。”
故事最终是以李燕生终于下决定要挖金子来给自己儿子看病,但发现金子已经不在了作为结局。这也应了那句话“一切没有出现过,一切也存在了”。或许压根就没有什么金子,而所谓的金子其实就是每个人的初心、良知。用孟子的话说,是因为外在环境的影响和世俗杂染使人放失了恻隐、礼让、羞恶、是非的仁义礼智四端之心。人这辈子就是要通过人生历练,来“求放心”,重新找回那被放失掉的四端之心。王阳明在孟子的良知说基础上提出了“致良知”的思想主张,实际也是为人的自我救赎指出一条路径。寻金之旅就是李燕生自我救赎之路,是她在生活的磨难中逐渐放失掉良知后,重新开始寻找初心的心路历程。从表面看,李燕生的金子不见了,寻金之旅失败了,但从内在看,初心良知就是人最可宝贵的金子,小说结尾处李燕生的寻金行为似乎隐喻着她正在找回自己放失掉的初心,找回那如金子般宝贵的良知。
最后想说的是,或许杨知寒真像自己说的那样是由着性子在写,没有什么深刻的想法,但其作品本身所达致的地方却已然赋予作品以深刻的内涵。